近日,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的第五轮和平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尚未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帝国坟场”的阿富汗迟迟无法迎来真正的和平,据联合国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战争和暴力冲突共夺走3804名平民的生命,其中包括927名儿童。这一年的平民死亡人数比2017年增加了11%,创下十年来最高纪录。在塔利班与美和谈的同时,全球各地区的暴力冲突事件仍在陆续发生。
在此背景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应邀来到中国。3月6日,在“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分析暨《全球安全文化》新书分享会”上,玛丽·卡尔多向大家谈起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研究与看法。

玛丽·卡尔多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在“全球治理”学科多有建树。当下,世界正在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其关键要素之一便是安全。基于对战争与安全文化的多年研究和深入了解,卡尔多使用了“全球安全”
(Global Security)
一词来指代应对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方式。
在由金城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安全与保密”书系首部作品《全球安全文化》中,卡尔多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文化”
(Global Security Cultures)
这一概念,揭示了它与“战略文化”、萨森的“集聚”、阿德勒和普利奥的“行动共同体”、布尔迪厄的“场域”以及福柯的“装置”等类似概念的关系,探讨了当前人类社会与民族国家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几种典型安全文化类型。
卡尔多从2001年发生在利比亚的空袭、《代顿和平协定》的签订和履行、阿富汗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等话题出发,向大家发问:尽管空袭并不能保护地面的普通民众,为何西方国家至今依然热衷于这种空袭模式?为何国际社会总是专注于和那些要为暴力行为负责的人士达成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定?(事实上,这种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定依然会让暴力继续。)为何明知毫无胜算,武装团体还要继续作战?为何当代的冲突与战争永无休止、难以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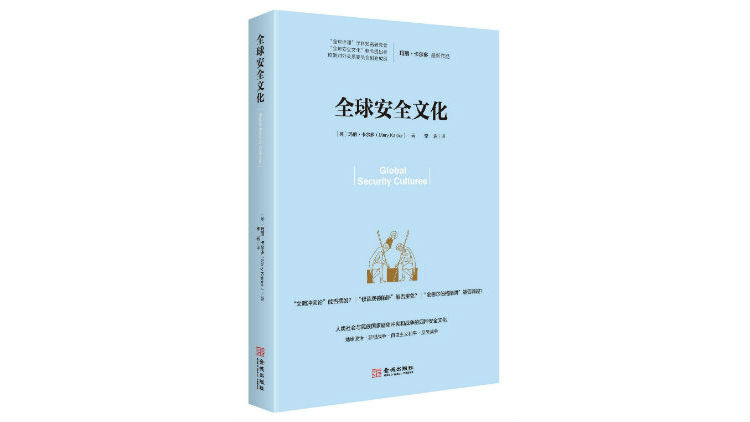
《全球安全文化》,作者:(英)玛丽·卡尔多,译者:李岩,版本:金城出版社,2019年4月。
“安全”是一个极为含糊不清的概念
在卡尔多写作这本书之时,她感觉存在着一种颇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不详预感,就好像20世纪糟糕的世界性悲剧又将重演一样。
事实上,这一悲剧已经在发生:难民溺亡于地中海,医院与医疗设施遭到轰炸,数千名青年男子(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遭到无人机、巡航导弹和战斗机的远程杀戮,神经毒气、燃烧弹及集束炸弹等被国际法禁止的可怕武器被投入使用,性奴死灰复燃,老百姓(603883)因遭遇围城而陷入饥荒,在拥挤的城市中货车和飞机被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无辜者遭到斩首、监禁与酷刑折磨。任何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人都希望上述现象永远消失。然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20世纪的那种战争,而是别的东西。

卡尔多试图解释这种“别的东西”。她使用了“全球安全文化”这一概念工具来帮助我们描述或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以便提出可能的解答。
在卡尔多看来,“安全”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与权威和权力密切相关。对于分析当前的形势而言,最能提供帮助的洞见在于意识到“安全”是一个极为含糊不清的概念。一方面,它意味着安定与无所顾虑。另一方面,它又指的是某种机构或一系列行动:门锁、机场扫描器、福利预算、警察、军队等等。
数百万人生活在深度不安全的状况下,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乌克兰,以及非洲的许多地方,都是如此。然而,国际社会对此的回应不仅仅是不适当的,还常常导致事态变得更加糟糕。一方面,对于不安全(尤其是恐怖主义袭击)这一问题的本能反应便是空袭或无人机轰炸。我们都知道,空袭从来不像声称的那样精准,总是会导致所谓“附带伤害”。我们还知道,空袭并不能终结不安全的状况,恰恰相反,无论对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阿富汗的塔利班,还是“伊斯兰国”而言,空袭总是被他们当作发动进一步恐怖袭击和征募人手的正当理由与依据。另一方面,人们还认为,空袭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与那些造成了不安全局面的战斗团体与残暴政权对话。
然而,我们知道,要想将此类团体聚集起来是极为困难的。此外,对话所达成的任何协定要想生效,都必须以巩固这些团体及政权的权势与地位为前提,由此不安全的状况也就将持续下去。我们还知道,此类协定所包含的国家构建及和平构建议程只会耗费大量资源,几乎从来不曾确立日常的安全状态。越来越多的批判性社会科学文献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标准回应方式的局限。然而,错误依然在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由此,卡尔多提出了“安全文化”,它深植于政治权威或各种权力关系的具体形式之中。并且“安全文化”是被建构出来的,可以被一次一次地复制。卡尔多认为,“文化”一词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某些活动看上去不合逻辑,也会变成习惯与规范。例如,在“9·11”事件发生16年之后,当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已变得前所未有地普遍,为何仍在使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分子?当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马里、索马里以及其他各地的战争令形势雪上加霜时,为何政客还会觉得战争是应对恐怖之道?为何叙利亚或是民主刚果等地的冲突永无休止?为何当显然毫无胜算时,武装团体还要继续作战?
卡尔多的论据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此类行为是有道理的;文化构造了叙事、职业生涯路径、物质激励与政治权力,并反复灌输思考及行事的方式,令其显得理所当然。因此,区分不同的安全文化、关注促成安全的不同方式,对于围绕着干涉战争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将干涉战争的各种方式都混为一谈,并认定无论如何应避免干涉战争。然而,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完全不干涉是做不到的。问题更在于,对战争的干涉是否经由国家或国际机构等政治权威掌控:其目的是在于终结战争,还是协助战争中的这一方或那一方;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达到上述目的。
四种典型的安全文化类型
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考察,卡尔多探讨了当前人类社会与民族国家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四种典型安全文化类型——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新型战争
(New Wars)
、自由主义和平
(Liberal Peace)
和反恐战争
(War on Terror)
冷战期间,“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是最主要的安全文化模式。它是一套关于权力游戏的语言,通常是各个国家追求和领土相关的利益的行为。换句话说,正如地缘政治思想家常常挂在嘴边的:地理即命运。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卡尔多引述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的名言:“战争创造了国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又创造了战争。”虽然地缘政治越来越不适用于当前的形势,但它依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文化,并且吸收了大量资源。

而所谓“新型战争”
(New Wars)
,是指演化自冷战时期地缘政治遭遇的主要挑战——革命战争,以及反暴动的回应方式。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争不同的是,在新型战争中,军阀取代了“有梦想”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份政治取代了左右派对抗的政治,而且身份尤为重要。它包括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兼具全球性和本地性的网络(例如民兵、军阀、犯罪集团、雇佣兵等,也包括些许常备军),使用的是捕获或引进的设备,尤其是简易爆炸装置和小型武器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武器装备。
新型战争在截然不同的行为框架内采用了新技术。在巴尔干、中东或是非洲等地参与现代战争的武装团体能够组成松散的网络或联盟,这主要得益于通信技术的改善。他们还有能力开发出所谓“非常规技术”,例如将日常原料和手机等复杂的引爆装置结合在一起的简易爆炸装置。只是,这些行为体不是从战争的胜败,而是从暴力行为本身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且,暴力直接针对的是贫民而非敌人,是为了掠夺资源而非保卫民众安全。如今,此类战争之间的相互联系愈发加强了,而且难以终结。
“自由主义和平”
(Liberal Peace)
起源于对地缘政治的反对,于1945年后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诞生,目的在于终结“战争之祸”,永远不再重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覆辙。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和地缘政治的复苏,对于这一国际新体制的希望很快就灰飞烟灭了。只是到了1989年后,自由主义和平才成为地缘政治安全文化之外的替代选项。它与特定的国际或地区组织有关(如联合国、欧盟、非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但是通过国家和私人行为体的参与得以落实的,包含一系列新的行动,即军事和民事人员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也就是达菲尔德所谓“战略复合体”——众多国际机构、维和部队、私人安保承包商、非政府组织,还包括重建和国家构建等一系列行为。

自由主义和平如今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困境。其主要行动之一是人道主义援助。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创立者之一贝尔纳·库什内
(Bernard Kouchner)
认为,总是存在着人道主义行动沦为战争共谋、承认交战各方的合法性、为民众提供食物却不顾导致其苦难的深层原因等危险。在他看来,人道主义机构的作用是“中介性”的:令人们关注受害者的痛苦处境,从而促使政府采取行动。20世纪80年代初的埃塞俄比亚饥荒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质疑之声:人道主义机构请求埃塞俄比亚政府许可自己接触忍饥挨饿的民众,考虑到这场饥荒正是政府蓄意制造的,而且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样的做法正确吗?人道主义机构越来越多地开始呼吁动用强力来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者,并建立可以令平民获得保护和援助的人道主义走廊和安全区域。这一观点在90年代渐渐获得了认同。
然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导致了这一立场的逆转。2003年8月19日,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遭到轰炸,备受尊敬的巴西外交官、联合国秘书长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
(Sérgio Vieira de Mello)
遇难,这一事件有时被称为联合国的“9·11”时刻。这起事件令人们注意到被认为在一场战争中站在某一方一边的危险,这样一来人道主义机构本身就会成为打击目标。在伊拉克、阿富汗和马里等地,自由主义和平战略复合体愈发被围墙和哨所封闭了起来,无法直接接触他们应该帮助的那些民众。卡尔多由此提出她的问题,那么该如何保护平民,而不是单纯将交战双方区分开?

在21世纪头十年结束之际,出现了通过反恐战争促成安全(或是不安全)的新方式,即利用大规模监视和无人机技术,执行远程“杀戮或俘虏”行动。“反恐战争”
(War on Terror)
是作为对所谓“非对称威胁”——恐怖主义、暴动,以及当代各种常常由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暴力,也就是新型战争——的回应而兴起的。这一新兴的安全文化包含了一系列新行动:重点从军队转变为情报机构与私人安保承包商相结合,广泛使用大规模监视、网络战争和机器人等新技术,以及突破曾被地缘政治奉为圭臬的一系列禁区(例如对定点清除和酷刑的反对)。反恐战争与“美国例外主义”紧密相关,尽管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沿着美国设定的路径前进。同时,存在着一个悖论:恐怖主义增加了反恐战争的合法性,反恐战争又使得恐怖主义更加猖獗。
自由主义和平的可能性
在解释完四种典型安全文化类型后,卡尔多以波黑、阿富汗、叙利亚为例,描绘了四种安全文化在不同的新型战争环境下的表现,来考察其各自的演化过程。
1992至1995年的波黑战争是首场引起国际关注的新型战争,自由主义和平的许多关键要素(及缺陷)都成形于这场战争中。1995年的《代顿协定》
(The Dayton Peace Agreement,此前被称为《波黑和平总框架协定》)
结束了波黑的战争,它常常被赞颂为一大胜利,是当代和平协定王冠上的宝石,也构成了自由主义和平安全文化的基石。

1995年,前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协定,结束了波黑战争。
不过,卡尔多认为:《代顿协定》的确结束了公开的暴力行为,但与此同时,它又认可了种族清洗造成的结果,并巩固了发起战争的种族主义军阀的权力。协定的捍卫者认为,这是终结战争的唯一方式。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国际谈判者从一开始就将军阀的种族主义假定认可为具有合法性的。谈判者提出了一系列分治建议,这实际上正合交战各方的心意。
以当时的首席谈判代表塞勒斯·万斯
(Cyrus Vance)
和戴维·欧文
(David Owen)
提出的计划为例。该计划将波黑分成了十个州,其中九个由某一种族支配,这为克族通过种族清洗来确保掌控自己支配的州的做法提供了合法性。据说,克族军事组织HVO,被解释成了“谢谢万斯和欧文”
(Thank you Vance Owen)
的简称。只是在种族清洗已经完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种族分治的局面后,《代顿协定》才有可能达成。的确有人指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了给最终协定创造条件,国际社会参与了合谋,例如克族重新夺取了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飞地,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戈拉泽等东部的安全区域也沦陷了。2009年,欧洲人权法院判定《代顿协定》侵犯了人权。
阿富汗仍未平息的暴力局势或许最为突出地彰显了“新型战争”的“永不停歇性”。卡尔多认为,自2001年开始,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演变成了新型战争、反恐战争和自由主义和平的结合体。而叙利亚的乱局是全世界伤亡最为惨重的,也是最为复杂的。自2001年开始,叙利亚的乱局结合了新型战争、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令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日复一日的悲剧更加严重。自由主义和平则被排挤到了边缘位置。人们常常表示西方未对叙利亚进行干涉。但事实上,各势力都对叙利亚进行了干涉。问题在于干涉的类型,卡尔多说。
满目疮痍的叙利亚
对此,卡尔多提出了她的核心论点: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取决于自由主义和平安全文化的演化。必须减少对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定与旨在将冲突各方分隔开来的维和行动的重视程度,转而更加重视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增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努力。这些举措包括保护平民、赋予司法机制更大的作用,以及更加重视发展和具有合法性的生存之道。她将这种方式称为“第二代人的安全”。尤其令卡尔多全神贯注的重点在于“个体安全”
(Individual Security)
而非国家安全的“人的安全”
(Human Security)
最后,卡尔多补充了书中未写到的涉及中国的内容。她认为,和其他大国的情况一样,地缘政治依旧主导着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过,中国在自由主义和平领域也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本文整理自玛丽·卡尔多的现场发言以及其新书《全球安全文化》中的相关内容。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编辑
覃旦思;校对:薛京宁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最新评论